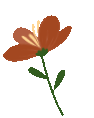惊梦相思人鬼情
不在梅边在柳边
第一章 引言 万历年间,程朱理学的教化风气日益增长“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深入人心,为对抗“理学”至上,弘扬解放人的个性,追求个体精神,对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此时正值万历28年,这一年汤显祖49岁,辞掉了历经四次求取的一职半位,闲居临川,目睹青年爱情遭遇,便开始创作《还魂记》又作《牡丹亭》。 早年的汤显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与权贵以势压人,恶意报复的丑陋面目有了清醒深刻的认识,这样的心路历程和科举报负也自然而然流露于《牡丹亭》中。剧中的杜宝,陈最良,柳梦梅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应试经历,也因此产生了差异极大的人生命运。也就此反映出汤显祖在官仕险途中屡屡碰壁,逐渐消解了其经世致用的雄心壮志,“情”与“志”被汤显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将满腔报国热情投注于戏曲创作之中。对于自我心中美好政治情怀的幻想和个人理想的解放之切最终促使汤显祖走上“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道路。而用“情”至深的《牡丹亭》一经问世,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而《牡丹亭》剧中并没有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婆婆和《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母亲那样真正意义上的明确的“反派角色”却极具戏剧色彩。剧中唯一的阻碍便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阴阳相隔,但在第廿三出《冥判》中,胡判官也被二人之情所感动,协助杜丽娘还魂。也应证了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的题词: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汤显祖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所体现的“至情”强而有力的批判封建“理学”思想。光怪陆离下,深刻描绘那时的社会本质,让现实中不可能的爱情得以实现,其解放个人个性的深刻思想内涵对当时社会有着强烈的冲击。 第二章 杜丽娘形象分析 从《牡丹亭》角色塑造来看,杜丽娘无疑是剧中“情” 的代表,作为南安太守的千金小姐,杜丽娘可谓是长期 饱受封建礼教的压制。她几乎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只得“终日绣房,长向花阴课女工”,甚至就连去自家后花园也不被允许,几乎是一种软禁式的生活。 至于情感需求,杜丽娘养在深闺,既不可能萌发爱情,也无真挚的友情, 即使是父母之亲也要深受封建礼制的约束。在这种环境下,杜丽娘显然极度缺乏自我主体意识,是深受封建理学压制人性的一个突出代表。 然而,当杜丽娘接触到《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便萌发了对美好爱情 的追求和“性”的意识觉醒,从而开始了自己在强大的封建礼教压制下的微弱反抗——《寻梦》但当她第二天醒来,发现只是一个梦,便非常怀念这个梦,怅然若失,念念不忘。只得只身一人,形影单只来到后花园,却发觉凄凉冷落,又无可奈何,便发出酸楚心声: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第十二出《寻梦》 于是她揽镜自照,心想,若自己不手自描画,日后谁能记住我杜丽娘,便自画春容,并题诗于上,寄托自己对于梦中柳面书生的无限遐思: “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第十四出《写真》 而在杜丽娘忧思去世之前,依然都在想念曾经的那个梦,魂牵梦萦,久久不忘,她唱到: “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怎能够,月落重生灯再红!”——第二十出《闹殇》 这些无一不体现着杜丽娘对于自我“梦”的追求和求而不得的深深的感伤,“至情”的种子也就此埋下,杜丽娘的目的也逐渐显明使得第卅五出的《回生》也显得那么合情合理。 爱情是人性中最迷人、最珍贵的情感,而杜丽娘却遭受了封建时代最残酷的压制。一切对美的向往、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都在封建伦理的压迫下,以各种方式不断被挤压和扭曲,导致最基本的人性丧失,成为统治阶级理想中的美德和贞节典范。 然而,杜丽娘的反抗毕竟是微弱的,但人性一旦觉醒,就势不可挡,因为在觉醒之后,杜丽娘并没有选择再次向封建礼教屈服,而是在一场无言的斗争中离开了世界,以另一种方式释放了她长期压抑的人性,宣示了“情”的力量和价值以及对封建伦理的批判。 第三章 杜宝形象分析 杜宝作为杜丽娘的父亲,一直严格奉行封建礼教规范,即使对女儿却也并没有体现出真诚的父爱。叹息道: “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第三出《训女》 只想着按照道德规范将杜丽娘培养 得“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以待“做门楣”。杜丽娘死后,尽管杜宝痛失爱女,但又恰巧高升安抚使,此时杜宝为朝廷尽忠的礼教思想显然压过了丧女之痛。而后当杜宝任上得知杜母为贼人所害的消息后,经过短暂的悲痛立马清醒过来: “夫人是朝廷命妇,骂贼而死,理所当然。我怎为她乱了方寸,灰了军心?”——第卌六出《折寇》 随后便不再悲痛, 而投入到御敌的下一步谋划中,其巨大的情感克制力令人可敬又可畏。最后当其见到生还后的杜丽娘时,其第一反应居然是: “此必花妖狐媚,假托而成。”——第五十五出《圆驾》 以至于柳梦梅感叹道: “好狠心的父亲,他做五雷般严父的规模, 则待要一下里把声名煞抹。”——第五十五出《圆驾》 由此可见,在杜宝的世界里,“理”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对于“人性”的价值和“情”的意义则予以否认和忽视,这与至情的杜丽娘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在这种尖锐的“情”“理”对立中, 汤显祖对于“情”和“人性”的大力赞扬与肯定的思想才得以升华。 第四章 《牡丹亭》“情”与“理”的艺术成就 爱情,是人性之美的突出代表,因此,汤显祖选择了爱情作为切入点,直接抨击封建理学的残酷和虚伪。杜丽娘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这座色彩斑斓的花园时,杜丽娘的生活本应是美满的,但她却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虚度了青春。只能假托于梦境来实现她对于人性的追求。只得无奈感叹: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面对这种现状,杜丽娘显然无力反抗,但已经觉醒的她又不甘于虚度一生,最终只得抑郁而终,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向这个世界做出了最后无言的反抗。 但如果剧情就此结束,《牡丹亭》的只字片语就仅仅是对程朱理学中对于“理”的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一次不那么有力的抨击,同时也意味着 “情”终究无法与“理”抗衡,难以体现出“情”的 价值和力量。因此,汤显祖大胆使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让死去的杜丽娘魂魄再次还魂,并与柳梦梅相恋,甚至得以死而复生,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此天马行空且具有神话色彩的情节设置在以往的现实主义剧作中实属罕见,但读来又感觉那么的合情合理, 原因就在于情节的背后有着“情”的力量的支撑。正是由于“情”的巨大力量,让杜丽娘可以遗梦而伤逝,又可以人鬼相恋起死回生,只要“情之至”了,连生死天命都可以超越。在最后的第五十五出《圆驾》中,汤显祖为剧作设置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由皇帝亲自“据奏奇异,敕赐团圆”,这就意味着杜丽娘与柳梦梅这段不合礼制的爱情得到了最高封建权威的认可,“理”在“情”的巨大力量下做出了妥协,“情” 则彻底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战胜了“理”。由此可见,汤显祖所设置的这个大团圆结局非但没有削弱《牡丹亭》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力度,反而进一步彰显了“情” 的力量和价值。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史,人性与传统伦理的矛盾始终贯穿其中。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市民阶级的成长,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然而,面对封建专制的空前强化和封建理学对于人性日益强烈的压制,“情”与“理”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且越来越尖锐,人性的解放需求也越来越突显,《牡丹亭》之所以能流芳千古,正是因为它充分抨击了封建伦理对人性的压抑,充分肯定了“情”的价值和意义,使《牡丹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人性的觉醒,具有超越古今中外的永恒价值,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